许多企业把所谓的“战略”变成了年度计划:加一点利润、降一些成本,或是扩大局部的市场份额。但在哈默尔看来,这只是战术性的修修补补,和真正的战略毫不相干。战略不是盯着后视镜开车,而是基于对未来的理解来塑造未来。《竞争大未来》提出的“战略意图”提醒我们:企业必须拥有超越现实的雄心,并通过长期能力积累,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有人问,今天战略是不是已经贬值了?谈论战略是否还有意义?
近些年来,确实有不少大公司直接撤掉了战略管理部门,或将其何必到企业管理部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现在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,所谓的战略文件往往还没落地,就已经被现实的变化或内部的阻力而颠覆了。
于是,有的企业抱怨说战略蓝图很好、但很难落地,也正是因为如此,很多企业干脆放弃战略,开始纷纷追逐眼前业绩的经营计划。
譬如通过兼并重组缩减规模、加大推销力度、或降本增效等措施来提高经营有效性等方式,达到每年利润增长百分之多少,成本降低几个点,市场份额增加几个百分点等等目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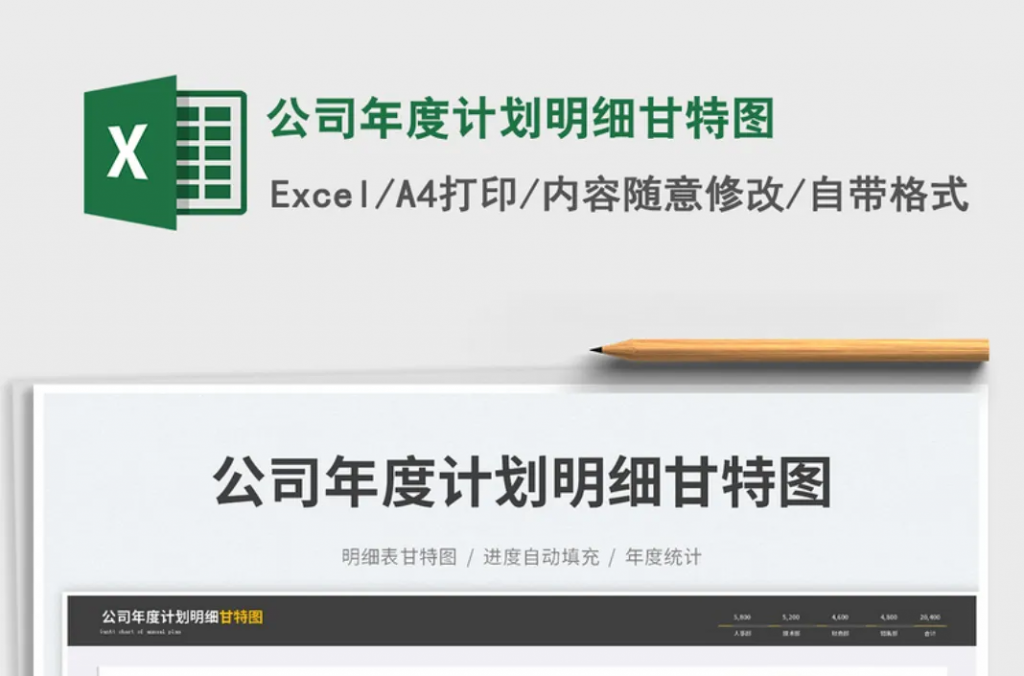
可在哈默尔看来,这哪里是什么战略?这些最多是一些例行公事的、功能性的战术计划,没办法让企业产生脱胎换骨的效果,更没有办法达到行业领先。
在许多公司,战略就意味着一年启动一次计划程序,所追求的不外乎根据过往的经营数据,修修补补,在这儿增加点利润,在那儿降点成本,或者在某处又发现了一个多赚些微薄利润的生意。
在飞速发展的今天,稍微清醒些的人都不会觉得,这样的战略规划能带来什么真正的价值。也难怪这样的“战略”在企业会不受广大群众的欢迎。
这时,我们才能重新理解哈默尔心中的价值:他告诉我们,这样的战略计划好像是一边要求司机盯着后视镜,一边往前开车。他认为,真正的战略是基于对未来的理解来塑造的。
战略并不是一纸计划,而是一种核心能力和长期的意图。真正的战略,是循序渐进,润物无声的能力增长过程,战略不是大规模的重组、更不是剧烈的变革,它应该流淌在整个组织的血液里。
今天,我们就从哈默尔与普拉哈拉德合著的经典之作——《竞争大未来》谈起。
1989年,哈默尔与普拉哈拉德在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上发表文章《Strategic Intent》,提出了战略意图(Strategic Intent)和核心竞争力(Core Competence)两个概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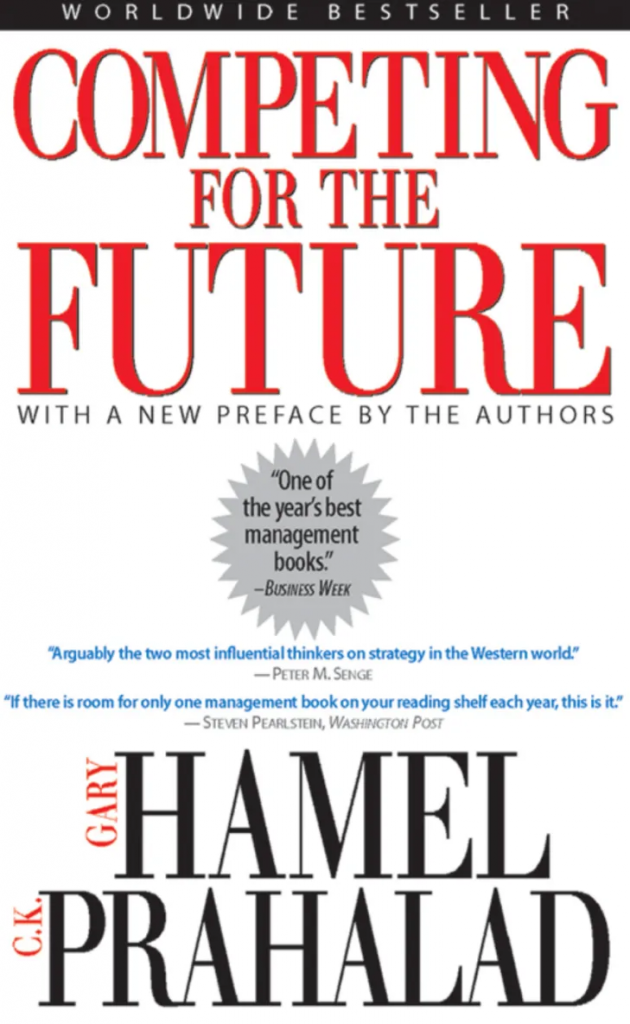
在传统战略框架中,企业往往被现有资源和行业格局束缚,战略更多是对经营有效性的提升,是对现实的被动回应。
但哈默尔强调,企业需要基于对未来的理解,确立超越现实的战略意图,并通过长期的能力积累,去塑造未来的行业格局。
这些理论不仅改变了战略管理的思考方式,也通过他们合著的代表作,1994年出版的《竞争大未来》(Competing for the Future)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,成为影响全球企业战略的重要著作。
■战略意图:超越现实的雄心
首先谈谈战略意图,所谓战略意图,指的是一种雄心,是说企业的战略不应受制于现有资源,而应当由对未来的一个远大的目标驱动,这个远大目标就是战略意图。
他认为,没有哪条戒律规定大多数公司必须是默默的跟随者,而不是领先者。而在商业领域的领先,并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不是意味着大家都一样,是要去抢同一个奖的竞争对手,而是意味着自己可以对这个奖是什么持不同的定义。
哈默尔举例说,在未来,奖品的数目有可能与选手的人数一样多,得奖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想象力。
无论是米开朗基罗、达芬奇、毕加索、梵高,还是张择端、齐白石、徐悲鸿都是成就卓著的画家,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创意与独特风格。一个画家的成功决不表明另一个画家注定要失败。
不过,这些艺术家身后都有一大群洋洋得意,自以为是的模仿者。
其实商界同艺术界一样,领先与落后,伟大与平庸之间的区别全在于对未来事物具有独特的想象力。
在中国,也有许多企业展现了战略意图的力量,如华为、比亚迪等。
- 华为:在早期缺乏核心资金、缺乏技术时,任正非就就设立了“要在全球通信产业中赢得尊重”的远大目标,坚持长期高强度研发投入,不断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革,最终成为行业的引领者。
- 比亚迪:早期从电池起步,却设定了“新能源领军者”的雄心,如今不仅在电动车销量上超越传统车企,还进入储能、半导体等新领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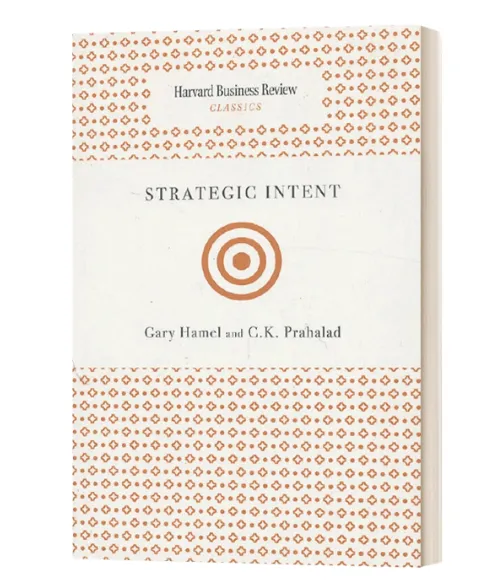
这些超越现实的目标,正是战略意图的当代表达。这些企业在发展的早期的资源都非常有限,却能摆脱那个行业赚多少钱、那块市场增长百分之几的眼前诱惑,凭借独特的“战略意图”不断聚合资源,推动长期创新。

